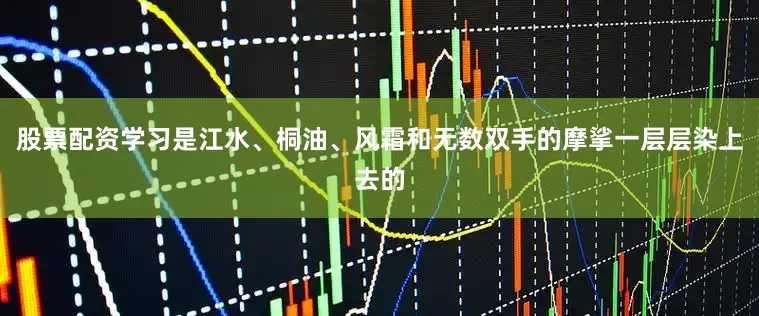
江雾在破晓前最浓,像一层浸了水的棉纱,沉沉地压在河面上。老周蹲在船头,手掌贴着潮湿的船板,掌心能感觉到木头吸饱了夜露后的微微膨胀。他的船很老了,船身乌黑,不是漆的,是江水、桐油、风霜和无数双手的摩挲一层层染上去的。船帮上深深浅浅的划痕里嵌着泥沙,指甲刮一刮,能抠出几粒细碎的河沙,不知是哪一年的洪水留下的。
天还没亮透,对岸的灯火稀稀落落,像几粒没燃尽的炭。老周摸出铜烟锅,烟袋里的烟丝早就干透了,搓一搓,簌簌地往下掉碎末。他划了根火柴,火光在雾气里晕开一小圈昏黄,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,映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。吸一口,烟从鼻孔里缓缓溢出,混进晨雾里,分不清哪是烟,哪是雾。
船桨横在船尾,桨柄被磨得发亮,木纹里渗着常年握出来的汗渍。老周的手指关节粗大,指节处结着厚茧,握桨的地方尤其硬,像是骨头自己长出了一层壳。他年轻时,村里人笑他的手像老树根,如今皮肤皴裂,纹路里总嵌着洗不净的黑,像是树皮裂开后露出的深褐色内里。
“老周,过河!”岸上有人喊。是个挑担的菜农,扁担两头挂着湿漉漉的青菜,叶尖还滴着水。老周没应声,只把烟锅在船帮上磕了磕,烟灰落进江里,瞬间被水流卷走。他站起身,船身微微一晃,脚下的木板发出沉闷的“吱呀”声,像是老人在叹气。
展开剩余67%渡船缓缓离岸,桨叶划开水面,水声黏稠,像是搅动一锅熬了太久的米粥。老周划船的动作很慢,却很稳,每一桨下去,水波便均匀地向两侧推开,船头破开的水纹像是一把钝剪刀裁开的布。菜农蹲在船头,手指拨弄着菜叶上的水珠,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老周说话。老周大多只是“嗯”一声,或者干脆不答,眼睛始终望着前方,仿佛雾里藏着什么只有他能看见的东西。
船到对岸,菜农摸出两枚硬币,老周摇摇头,指了指船头的陶碗。碗里积着薄薄一层水,底下沉着几枚锈迹斑斑的硬币,像几片干涸的鱼鳞。菜农把钱丢进去,“叮”的一声,碗里的水纹颤了颤。
日头渐渐高了,雾散了些,江面浮起一层细碎的金光。老周坐在船尾,从怀里摸出半个冷馒头,掰碎了丢进水里。鱼群立刻聚拢过来,水花翻动,银白的鱼脊在阳光下闪闪烁烁,像许多小小的刀片划开水面。他望着,嘴角微微扯了扯,像是在笑,又像只是被风吹皱了脸。
晌午时,村里的小孩跑来江边玩。他们不敢靠近老周的船,只远远地站着,往水里扔石子。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胆子大些,蹲在岸边问:“爷爷,你的船怎么是黑的?”老周低头看了看船身,乌黑的木板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,像是涂了一层釉。他伸手摸了摸,木头早已没了最初的纹理,只剩下无数道划痕和补丁。
“不是黑的,”他说,“是江水染的。”
小女孩似懂非懂,又问:“那它原来是什么颜色?”老周怔了怔,忽然想起很多年前,这船刚造好的时候,是枣红色的。新刨的木头散发着淡淡的松香,船帮上的红漆亮得能照出人影。那时他二十出头,第一次撑船,手心磨出了血泡,却还是咧着嘴笑。
可现在,他记不清了。
傍晚,最后一趟渡船靠岸后,老周没有立刻回家。他坐在船头,望着江水发呆。夕阳把江面染成橘红色,波纹荡漾时,像是有人在水下点了一盏灯。远处,新修的大桥上车来车往,车灯在暮色里连成一条流动的光带。老周摸出烟锅,却发现烟袋已经空了。他叹了口气,把烟锅在船帮上轻轻敲了敲,像是敲一扇不会再开的门。夜里,江上起了风。老周的船拴在岸边,缆绳被风吹得“咯吱”作响。船身轻轻摇晃,像是梦里的人在翻身。月光照在乌黑的船板上,那些划痕和补丁在阴影里格外清晰,像是老人脸上的皱纹,每一道都刻着年月。
第二天清晨,人们发现老周的船不见了。岸边只留下几道拖痕,像是船自己爬上了岸,又悄悄滑进了水里。下游的渔夫说,天蒙蒙亮时,看见一条枣红色的船顺流而下,船头站着个挺直腰板的人影,在晨光里渐渐淡去。江水无声无息,几片落叶打着旋儿,漂向远方。
□罗依衣
(责编:温文)
发布于:山西省万隆优配-能加杠杆的炒股软件-配资门户平台官网-炒股炒股配资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